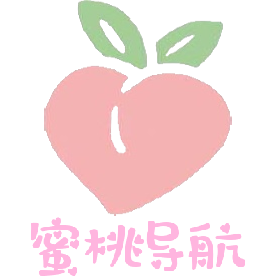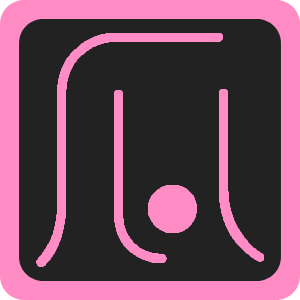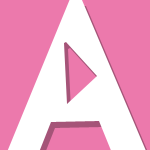站长推荐
星空入口
帝王会所
蜜桃导航
黑料福利网
吃瓜黑料网
第一导航
萝莉岛VIP
暗夜入口
小嫂嫂导航
猛男研究所
狼友福利网
黑料概念站
欲女自慰馆
万色广场
外网禁区
51福利网
TikTok入口
熟女超市
秘密研究所
全球福利汇
乱伦偷拍网
福利淫地
91福利社
初一小萝莉
换妻会所
中文情色网
三千佳丽
B站入口
隐秘部落
色色研究所
热门搜索
站长推荐
六朝清羽记 第十三集 第八章
第八章 ◆ 红粉
华灯初上,一行人来到宅前。萧遥逸此行与上午单独来访大是不同,前面四名护卫开路,后面十几名仆役提着灯笼,打着火把,牵着黄狗,背着雕弓,还有几个胳膊上架着鹰,手里提着鸟笼,鞍旁挂着酒囊、箭矢,一行人鲜衣怒马,浩浩荡荡,兴师动众。
程宗扬正怀疑他会不会来,看到这阵势不禁吓了一跳∶“小侯爷,你这是要出门打猎?,”
萧遥逸戴了一顶玉冠,两缕乌亮的鬓发从耳畔长垂及胸,更显得面如冠玉,风流局傥。他眼睛还有些发红,脸上却若无其事∶“打什么猎啊。我这人怕黑,人多了好壮胆。走吧,程兄。”
“公子。”秦桧把坐骑牵来,躬身施礼,却用眼神示意程宗扬是否要带几个人去。
程宗扬接过缰绳,微微摇头。他想探探这位小侯爷的底细,带的人多反而不便。
萧遥逸在马上弯下腰来,一只眼俏皮地眨了眨,笑道∶“程兄,你那位美婢不带上吗?”
带上小紫,这顿饭就不用吃了。有她在,吃饭时,房塌楼倒这种诡异的倒霉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用管她,”程宗扬翻身上马,笑道∶“小侯爷请。”
萧遥逸一边催动坐骑,一边道∶“程兄这匹马不错。虽然身量不大,但耳尖腿直,鼻正眼明,像是五原城出的良驹。”
程宗扬心悦诚服地说道∶“小侯爷好眼光。”
萧遥逸挺起胸膛,一脸自负地说∶“玩鹰走马,可是我的绝技。你瞧我这匹白水驹,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足足花了我两千金铢才买到。还有这鹰可是难得的海东青,双翅如铁,上百斤的黄羊也能一口叼起。”
两人边行边谈,萧遥逸口若悬河,虽然有点夸夸其谈,却丝毫不惹人讨厌,就像孩子吹牛一样,让人觉得有种可喜的真诚。
程宗扬留心看着周围的景物。建康是晋国都城,建康城却与自己想像中完全不同。整个建康并非一座完整的大城,而是由十余座互不相连的小城组成。最大的当然是皇宫所在的台城,台城以南经过槐柳掩映的御道,出朱雀门后便是秦淮河。御道两侧官署林立,宰相府却在城外单独建了一座东府城。另外还有丹阳城、白下城、江乘城……星罗棋布,就像宫城的卫星城,与城间的宅院一起,连成一片繁华都市。
建康毗邻大江,水运极为发达,河港密如蛛网,便是海船也能直抵城中。晋国权贵的豪奢天下知名,街市繁华自不用说,就是普通行人也穿着镶嵌珍珠的丝履,宽袍大袖,风度翩然。
“建康东西南北各有四十里,城中人口有二十八万户。称得上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富甲一方。”
萧遥逸说这番话时,口气中并没有多少对自己所在这座城市的自豪,反而充满了嘲讽。
程宗扬与萧遥逸并辔而行,笑道∶“萧兄似乎不怎么喜欢这里?”
“建康锺山龙盘,石头虎踞,承平日子过久了,把人都养成了废物。”萧遥逸举起马鞭,“前面那条渠就是青溪,从城北的玄武湖注入秦淮河。城中的酒囊饭袋大都住在青溪和潮沟。”
正说着,一群贵族子弟从巷中出来,他们身着乌衣,大袖飘飘,人物俊雅不凡。只是半数都涂脂敷粉,不过出门几步,身边还要奴仆搀扶。
萧遥逸踩着马蹬站起身,大声叫道∶“饭桶!”
那些贵族子弟大笑着回道∶“小侯爷,天色已晚还不早些回去,小心侯爷的鞭子!”
萧遥逸悻悻坐下,程宗扬道∶“这些是什么人?”
一名随从笑道∶“那便是乌衣巷了。”
“乌衣巷?”程宗扬愕然道∶“王谢家族的子弟?”
萧遥逸哼了一声,“这些酒囊饭袋,白白生了一身好皮囊,”说着他压低声音,“难怪艺哥不屑与他们为伍!”
程宗扬讶然举目,萧遥逸口气虽然忿懑却刻意收拢声音,周围随从虽众,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听到。
萧遥逸微微一笑,彼此会意,接着一扬马鞭∶“程兄,我与你试试马匹的脚力!”
一行人扬鞭疾行,人如虎马如龙,踏破了青溪渠畔的夜色。
越往南行,人口越发稠密。此刻正是掌灯时分,街市上行人往来如织,若不是有四名护卫在前面开路,几乎寸步难行。
萧遥逸一抖缰绳,坐骑跃起,蛟龙般跃上河堤,冲向河滩。程宗扬骑术比他差了一百多倍,正犹豫要不要追上去,黑珍珠却被引发了好胜的性子,不等主人催动便抖擞鬃毛,追着萧遥逸的白水驹越过河堤。
两骑一前一后,不多时就奔出数里,将那些护卫、随从远远甩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月光下,青溪汇入河中,宽阔的河水邻邻闪动波光,不时有挂着彩灯的画舫楼船从河中泛过,船桨在水中划出道道静谧的波痕。
萧遥逸一直冲到河中才勒停马匹,脚下几乎触到水面,回身笑道∶“痛快!痛快!程兄,这匹马可比你的骑术高明。”
南荒丛林茂密,马匹驰骋不开,程宗扬还是第一次纵马狂奔。他喘着气拍了拍黑珍珠的颈子,“都是托它的福。若不是它跑得够稳,我这会儿早摔下来七八次了。”
萧遥逸大笑着扔下缰绳,然后朝一艘迤逦行来的画舫高声道∶“芝娘!”
一个红袖红衫的丽人从舷窗探身出来,扬起丝帕笑道∶“原来是小侯爷!快些靠岸。”
萧遥逸显然是这艘画舫的熟客,把缰绳扔给小厮,让他在沙滩照看马匹,自己和程宗扬一同踏上画舫。
那个叫芝娘的丽人摇摇摆摆迎上来,笑道∶“小侯爷,今日有空来河上散心了。”
萧遥逸笑道∶“两日不见,芝娘又水灵了。这是我的好友程公子,听说你舟上的佳丽冠绝秦淮,特意前来拜访。”
“小侯爷又替芝娘说了大话,若是程公子不满意,说不定还拆了奴家的画舫呢。”
芝娘向程宗扬福了一福,抿嘴笑道∶“程公子一表人才,难怪刚才灯花爆了两爆,原来是应在小侯爷和程公子身上。”
芝娘将两人迎到舟上。画舫分为两层,上面一层是一个两丈宽的通间,极为宽敞,四周雕梁画楝、珠帘翠幕,虽然不是十分豪奢,也别有一番雅致。
萧遥逸嘻笑几句,然后道∶“我和程兄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去备上好酒,整治几样精致的小菜,一会儿送上来,让我和程兄把酒言欢。”
芝娘一笑退下,把船楼留给他们两人。
建康把椅子称为胡床,用的人还很少。画舫里临窗摆着两张小几,坐具是锦边茵面的象牙席。萧遥逸随意地坐在茵席上,从袖中取出一柄洒金折扇,轻轻蝙着,意态从容,举止潇洒。
程宗扬笑道∶“小侯爷有意甩开随从,想必是有话要说。”
萧遥逸舒了口气,“程兄这么明白,大家就能少说很多废话了。”他合起折扇,注视着程宗扬的眼睛,慢慢道∶“那位姑娘,是岳帅的后裔吧?”
程宗扬没有答是,也没有答否,而是笑着反问道∶“萧兄怎么看出来的?”
萧遥逸神色黯然,“艺哥好几年都没有回过星月湖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做什么,可谁都没有帮他……”他揉了揉眼睛,勉强笑道∶“那位姑娘身上有岳帅的影子。艺哥到南荒是去找她的吧?”
程宗扬笑着岔开话题∶“我听说贵派生意做得也不小。”
萧遥逸何等聪明,一听就知道程宗扬对自己的身份还有怀疑。
“程兄谨缜些是应该的。我们星月湖不是什么帮会宗派,大家都是岳帅身边的人,岳帅离开后不愿分开,才聚在一起。大哥孟非卿,二哥侯玄,谢艺是我三哥,我排行 第八。说实话 ,我们这些人里,会做的生意没几个。只不过手下的兄弟都是军士出身,能吃苦,所以才办了船行和车马行。另外大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喜欢蹴鞠,又在晴洲办了家鞠社。”
“不是临安的吗?”
“你说七星社?”萧遥逸苦笑道∶“艺哥可能没跟你说。由于岳帅的死因,我们八兄弟分成两派,二哥侯玄、七哥王韬,还有我认为岳帅并没有死,四哥斯明信、五哥卢景和六哥崔茂认定岳帅已死,发誓要报复岳帅的仇人。因为这样,四哥和二哥闹的不说话。艺哥在晴洲伤了心,才远走临安加入七星社。”
程宗扬问道∶“你认为岳帅没有死?”
萧遥逸眼神一瞬间变得锋利无比,彷佛出鞘的利剑,决然道∶“见到岳帅遗体之前,我绝不信岳帅已经过世!”
萧遥逸神情激昂起来,“岳帅生前已经没有敌手!宋主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小儿,岳帅兵权在握,又立下大功,谁能撼动他的地位!宋主一封诏书,岳帅就慨然赴死,以为岳帅是傻的啊!我萧遥逸绝对不信!”
这个世界里,岳鹏举的宿命之敌秦桧正在自己手下办差,听萧遥逸的口气,高宗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即使以宿命论,岳帅也不该死。
程宗扬摸了摸下巴。“也许岳帅对那位宋主忠心耿耿呢?”
“忠心个屁!”萧遥逸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岳帅当初差点把宋主的母后收为姬妾,后来觉得名声不好,才没有大张旗鼓的娶韦太后过门。”
程宗扬又惊又笑,“还有这种事?那位韦太后答应吗?”
“岳帅决定的事,哪儿有她说话的分。不过岳帅那段日子有一半时间都在宫里住。直到韦太后肚子大了才搬出来。”
程宗扬心里一震,“岳帅还有个女儿?”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王哲托自己照料岳帅的后人,原来以为只有月霜一个,现在不但多了个小紫,还蹦出来一个没听说过的女儿。月霜是想杀自己没杀死,小紫是自己想上没上成,这两个已经够自己头痛的了,剩下这个鬼知道还会出什么妖蛾子。
“可不是嘛。”萧遥逸颓然道∶“岳帅三个女儿,一个被王哲王大将军在军中抚养,一位就是这个没有名分的小公主,岳帅死时她才三岁,可能宋主觉得脸上无光,把她藏起来,后来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还有一个,我们刚刚才知道是在南荒。”
“艺哥离开星月湖的时候,骂我们可耻,让岳帅的子裔飘零四方,对不起岳帅,骂的一点都没错。可王哲执意不给,我们也没办扶。韦太后生的又不知下落——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干,我和五哥还去找过韦太后,可一问她就哭,我们总不好对岳帅的女人动刑吧。最后这个……”
萧遥逸说着忽然离席,对程宗扬深施一礼。
程宗扬连忙道∶“这可不敢当。能在南荒找到小紫都是谢艺的功劳,跟我没什么关系。”
“程兄客气了。我是谢公子的人品,”萧遥逸叹道∶“岳帅这个女儿美貌绝伦,程兄却能相守以礼,小紫姑娘至今还是完璧之身吧?程兄如此光风霁月,令小弟佩服得五礼投地。”
程宗扬眼圈差点红了,萧遥逸如果不提,他还不知道自己竟然这么高尚。这事不是自己够君子,实在是小紫太狡猾……
程宗扬抹了抹眼睛,大度地说道∶“这一路确实是千辛万苦,不过都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萧遥逸笑着挤挤眼睛∶“程兄这一路和尚当得够辛苦,今晚定要让程兄好好乐上一乐。芝娘。”
芝娘在下面娇滴滴应了一声。“小侯爷,酒菜来了。”
小婢捧着酒菜上来,放在案上。
萧遥逸道∶“这种小盏如何尽兴?换大盏来!”
不多时,小婢送来大盏。萧遥逸屏开小婢,亲手给程宗扬斟酒,一边笑道∶“芝娘的画舫在秦淮河只能算平常,达官贵人去的画舫都是三五层高的楼船,我不惯里面那些娼妓拿矫作态,写写诗弹个曲就用一晚上,花了上百银铢,连手都碰不着,还自称风雅。我当不得那种冤大头,还是在这里自在!”
这位小侯爷果然是个趣人,程宗扬不由抚掌大笑。
萧遥逸扯开衣领,豪气万丈地说道∶“程兄,今晚我们不醉无归!”
程宗扬也不推辞。他拿起酒盏,目光从萧遥逸颈中扫过,不由一顿。
萧遥逸脖颈上刺着“有种”两个字,上午自己只看到萧遥逸的侧颈,这会儿才发现“有种”后面还有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句话∶“有种朝这儿砍”!
那几个字书法不算上佳,但写得飞扬跋扈、狂气十足,“砍”字最后一笔还被勾画成一把滴血快刀的形状。配上那句话的口气,很有种兵痞的无赖风采,与萧遥逸这种公子哥的风流之态反差极大。
程宗扬一见之下,禁不住放声大笑,指着萧遥逸的脖颈道∶“萧兄怎么想刺上这句话?”
萧遥逸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脖颈,“我到星月湖那年才十岁,岳帅让我住在他贴身卫士的营帐里。那天我一进去,就看到六七个老兵正在玩一种纸片,他们都精赤上身,脖颈、胳膊、大腿、后背都带着刺青,嘴里骂骂咧咧全是粗话。有个脸色阴沉的汉子打输了,二话不说,拿刀就在胳膊上划了一道,鲜血淋漓,可真把我给吓住了。”
“我在旁边大气也不敢出,不小心放了个屁,被个大胖子狠瞪一眼,差点吓得我尿裤子。后来一个粗豪的汉子过来,问我是不是萧遥逸,我说是,他说他叫孟非卿,是这群人的老大。”
“孟老大跟我说,这些人都是岳帅军中的好汉,我这样白白净净像个丫头片子可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也刺个青吧。有个肩膀上刺着骷髅头的汉子就过来,说他叫谢艺,皇图天策出身,军里就数他字写得好,连岳帅也比不过他,然后替我写了这句话,让人替我刺到脖子上。”
“不对啊,”程宗扬道∶“谢艺身上没什么刺青啊?”
“可不是嘛!”萧遥逸眼圈一红,委屈地说∶“等我刺完,那帮家伙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听说我是个公子哥,故意摆出阵势来吓我。他们身上的刺青全是假的,都是拿墨写上去的。那个大胖子是侯玄,脸色阴沉的汉子是斯明信,他划那一刀也是假的,弄的是鸡血。结果八个人里就我有刺青。”
程宗扬大笑道∶“谢艺也会捉弄人?”
萧遥逸悻悻道∶“他还说自己字好,其实字最好的是七哥王韬,他们太原王氏书法是家传的,真让他写这个六个字,起码值六百银铢,我也不用哭了。后来我找个机会,趁晚上把他们有胡子的全剪了,没胡子的画了个须子。本来我还想给艺哥打个耳洞戴上耳环,结果被他发现了,挨了他一顿打,我就往他被子里塞了一窝老鼠。”
萧遥逸说起自己的恶作剧,不禁得意非凡。渐渐的,他声音低沉下来,程宗扬知道他想起谢艺,心中伤感,便拿起酒盏向萧遥逸一敬,一饮而尽。
这时他已经不再怀疑萧遥逸的身份,只不过……“萧兄十岁就到了岳帅的大营,这年龄真够小的。”
“还不是因为我爹,”萧遥逸抱怨道∶“老头儿怕我在家里跟那些人一样学成废物,哄我说有个姓岳的,那里好玩,才把我骗过去。”
程宗扬想起遇到的王谢子弟,“是那些涂脂抹粉的家伙?”
“可不是嘛。那帮子弟大都是些饭桶,行动脂粉不离手,还自负得很,整天拿个拂尘东游西荡,说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真到做事的时候连屁都不会!”
程宗扬笑道∶“听说建康的贵族盛行服食五石散?”
“五石散是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种石头制成,岳帅当年也制过,到底没敢服用。建康城服的人倒是不少。五石散服过之后身上先热后冷,还不能吃热食穿厚衣,不管天多冷都要穿单衣,喝凉水,有些还要伏冰卧雪。而且服过之后要多走,称行散,停下来就要多喝酒,多吃东西。”
萧遥逸给程宗扬斟上酒,笑道∶“五石散那东西,服之令人神智恍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上次我去阮家,正遇上阮家兄弟在服五石散,他们服过五石散,然后先用凉水冲澡,接着开始饮酒。喝到一半,阮家兄弟觉得用杯子不过瘾,用个七尺的大盆盛满酒放在院子里,诸阮就围着盆子狂饮。正喝着一群猪过来,阮家兄弟也不嫌脏,就和那些猪挤在一起饮酒。饮到兴起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妾婢叫来,在院里交相淫乱。”
萧遥逸笑着摇头,“我萧遥逸再荒唐,也荒唐不到那地步。可大家提到阮家兄弟就说他们是狂狷天性,风流人物。提起我这位小侯爷,大家都说是不成器的荒唐子弟。这也太不公平了!”
程宗扬笑道∶“这多半是因为小侯爷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吧。”
萧遥逸大笑道∶“不错!程兄果然是萧某知己!诸阮的狂狷我倒不在乎,礼法岂是为吾辈所设!但不做事还要搏取好名声,这就太过分了。那些无知小子怎能缚住我鲲鹏之翅!”
萧遥逸举盏一口喝干,把酒盏扔到几上,叫道∶“芝娘!我要的佳人呢?”
芝娘上来,未语先笑∶“小侯爷莫急。我已经让人去接丽娘,就快到了。”
萧遥逸道∶“怎么不在你舟中候着?”
“丽娘吃不得苦,在舟上两个时辰就要靠岸歇息。”芝娘笑着向程宗扬解释,“奴家画舫新来了个粉头,名叫丽娘,年纪虽然略大了些,却是好风情,遍体风流。少顷来了,让她敬公子一杯。”
萧遥逸一把搂住芝娘,把她抱在膝上笑道∶“那个丽娘就让给程兄,今晚你陪我好了。”
芝娘笑着拈起一粒葡萄,含在唇间送到萧遥逸嘴里,低笑道∶“秦淮河三千画舫,粉黛无数,小侯爷这样的人才,那些粉头便是倒贴也肯。小侯爷却总照顾奴家的生意,奴家感激不尽。让奴家陪一晚,是奴家的福气。”
萧遥逸抹了抹她鲜红的唇瓣,笑道∶“嘴巴可真甜。我喜欢你这里是免得撞上熟人,让他们整天在我爹耳边聒噪。何况还有芝娘你这样的美人儿。”
芝娘却羞涩起来,柔声道:“奴家去更衣,再来陪小侯爷。”
萧遥逸放开她,与程宗扬饮了几杯,才道∶“芝娘这里酒菜从不掺假,而且嘴巴极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从不多说。还有一桩……”
萧遥逸好看地一笑∶“芝娘这人其实做不得这营生,她心肠太软,从不打手下的粉头。若不是我,她这画舫早就关门多时了。”
程宗扬笑道∶“看不出萧兄还这么怜香惜玉。”
萧遥逸大笑道∶“这话我爱听,来,程兄,我敬你一杯!”
两人推杯换盏,谈笑无禁。
华灯初上,一行人来到宅前。萧遥逸此行与上午单独来访大是不同,前面四名护卫开路,后面十几名仆役提着灯笼,打着火把,牵着黄狗,背着雕弓,还有几个胳膊上架着鹰,手里提着鸟笼,鞍旁挂着酒囊、箭矢,一行人鲜衣怒马,浩浩荡荡,兴师动众。
程宗扬正怀疑他会不会来,看到这阵势不禁吓了一跳∶“小侯爷,你这是要出门打猎?,”
萧遥逸戴了一顶玉冠,两缕乌亮的鬓发从耳畔长垂及胸,更显得面如冠玉,风流局傥。他眼睛还有些发红,脸上却若无其事∶“打什么猎啊。我这人怕黑,人多了好壮胆。走吧,程兄。”
“公子。”秦桧把坐骑牵来,躬身施礼,却用眼神示意程宗扬是否要带几个人去。
程宗扬接过缰绳,微微摇头。他想探探这位小侯爷的底细,带的人多反而不便。
萧遥逸在马上弯下腰来,一只眼俏皮地眨了眨,笑道∶“程兄,你那位美婢不带上吗?”
带上小紫,这顿饭就不用吃了。有她在,吃饭时,房塌楼倒这种诡异的倒霉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用管她,”程宗扬翻身上马,笑道∶“小侯爷请。”
萧遥逸一边催动坐骑,一边道∶“程兄这匹马不错。虽然身量不大,但耳尖腿直,鼻正眼明,像是五原城出的良驹。”
程宗扬心悦诚服地说道∶“小侯爷好眼光。”
萧遥逸挺起胸膛,一脸自负地说∶“玩鹰走马,可是我的绝技。你瞧我这匹白水驹,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足足花了我两千金铢才买到。还有这鹰可是难得的海东青,双翅如铁,上百斤的黄羊也能一口叼起。”
两人边行边谈,萧遥逸口若悬河,虽然有点夸夸其谈,却丝毫不惹人讨厌,就像孩子吹牛一样,让人觉得有种可喜的真诚。
程宗扬留心看着周围的景物。建康是晋国都城,建康城却与自己想像中完全不同。整个建康并非一座完整的大城,而是由十余座互不相连的小城组成。最大的当然是皇宫所在的台城,台城以南经过槐柳掩映的御道,出朱雀门后便是秦淮河。御道两侧官署林立,宰相府却在城外单独建了一座东府城。另外还有丹阳城、白下城、江乘城……星罗棋布,就像宫城的卫星城,与城间的宅院一起,连成一片繁华都市。
建康毗邻大江,水运极为发达,河港密如蛛网,便是海船也能直抵城中。晋国权贵的豪奢天下知名,街市繁华自不用说,就是普通行人也穿着镶嵌珍珠的丝履,宽袍大袖,风度翩然。
“建康东西南北各有四十里,城中人口有二十八万户。称得上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富甲一方。”
萧遥逸说这番话时,口气中并没有多少对自己所在这座城市的自豪,反而充满了嘲讽。
程宗扬与萧遥逸并辔而行,笑道∶“萧兄似乎不怎么喜欢这里?”
“建康锺山龙盘,石头虎踞,承平日子过久了,把人都养成了废物。”萧遥逸举起马鞭,“前面那条渠就是青溪,从城北的玄武湖注入秦淮河。城中的酒囊饭袋大都住在青溪和潮沟。”
正说着,一群贵族子弟从巷中出来,他们身着乌衣,大袖飘飘,人物俊雅不凡。只是半数都涂脂敷粉,不过出门几步,身边还要奴仆搀扶。
萧遥逸踩着马蹬站起身,大声叫道∶“饭桶!”
那些贵族子弟大笑着回道∶“小侯爷,天色已晚还不早些回去,小心侯爷的鞭子!”
萧遥逸悻悻坐下,程宗扬道∶“这些是什么人?”
一名随从笑道∶“那便是乌衣巷了。”
“乌衣巷?”程宗扬愕然道∶“王谢家族的子弟?”
萧遥逸哼了一声,“这些酒囊饭袋,白白生了一身好皮囊,”说着他压低声音,“难怪艺哥不屑与他们为伍!”
程宗扬讶然举目,萧遥逸口气虽然忿懑却刻意收拢声音,周围随从虽众,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听到。
萧遥逸微微一笑,彼此会意,接着一扬马鞭∶“程兄,我与你试试马匹的脚力!”
一行人扬鞭疾行,人如虎马如龙,踏破了青溪渠畔的夜色。
越往南行,人口越发稠密。此刻正是掌灯时分,街市上行人往来如织,若不是有四名护卫在前面开路,几乎寸步难行。
萧遥逸一抖缰绳,坐骑跃起,蛟龙般跃上河堤,冲向河滩。程宗扬骑术比他差了一百多倍,正犹豫要不要追上去,黑珍珠却被引发了好胜的性子,不等主人催动便抖擞鬃毛,追着萧遥逸的白水驹越过河堤。
两骑一前一后,不多时就奔出数里,将那些护卫、随从远远甩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月光下,青溪汇入河中,宽阔的河水邻邻闪动波光,不时有挂着彩灯的画舫楼船从河中泛过,船桨在水中划出道道静谧的波痕。
萧遥逸一直冲到河中才勒停马匹,脚下几乎触到水面,回身笑道∶“痛快!痛快!程兄,这匹马可比你的骑术高明。”
南荒丛林茂密,马匹驰骋不开,程宗扬还是第一次纵马狂奔。他喘着气拍了拍黑珍珠的颈子,“都是托它的福。若不是它跑得够稳,我这会儿早摔下来七八次了。”
萧遥逸大笑着扔下缰绳,然后朝一艘迤逦行来的画舫高声道∶“芝娘!”
一个红袖红衫的丽人从舷窗探身出来,扬起丝帕笑道∶“原来是小侯爷!快些靠岸。”
萧遥逸显然是这艘画舫的熟客,把缰绳扔给小厮,让他在沙滩照看马匹,自己和程宗扬一同踏上画舫。
那个叫芝娘的丽人摇摇摆摆迎上来,笑道∶“小侯爷,今日有空来河上散心了。”
萧遥逸笑道∶“两日不见,芝娘又水灵了。这是我的好友程公子,听说你舟上的佳丽冠绝秦淮,特意前来拜访。”
“小侯爷又替芝娘说了大话,若是程公子不满意,说不定还拆了奴家的画舫呢。”
芝娘向程宗扬福了一福,抿嘴笑道∶“程公子一表人才,难怪刚才灯花爆了两爆,原来是应在小侯爷和程公子身上。”
芝娘将两人迎到舟上。画舫分为两层,上面一层是一个两丈宽的通间,极为宽敞,四周雕梁画楝、珠帘翠幕,虽然不是十分豪奢,也别有一番雅致。
萧遥逸嘻笑几句,然后道∶“我和程兄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去备上好酒,整治几样精致的小菜,一会儿送上来,让我和程兄把酒言欢。”
芝娘一笑退下,把船楼留给他们两人。
建康把椅子称为胡床,用的人还很少。画舫里临窗摆着两张小几,坐具是锦边茵面的象牙席。萧遥逸随意地坐在茵席上,从袖中取出一柄洒金折扇,轻轻蝙着,意态从容,举止潇洒。
程宗扬笑道∶“小侯爷有意甩开随从,想必是有话要说。”
萧遥逸舒了口气,“程兄这么明白,大家就能少说很多废话了。”他合起折扇,注视着程宗扬的眼睛,慢慢道∶“那位姑娘,是岳帅的后裔吧?”
程宗扬没有答是,也没有答否,而是笑着反问道∶“萧兄怎么看出来的?”
萧遥逸神色黯然,“艺哥好几年都没有回过星月湖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做什么,可谁都没有帮他……”他揉了揉眼睛,勉强笑道∶“那位姑娘身上有岳帅的影子。艺哥到南荒是去找她的吧?”
程宗扬笑着岔开话题∶“我听说贵派生意做得也不小。”
萧遥逸何等聪明,一听就知道程宗扬对自己的身份还有怀疑。
“程兄谨缜些是应该的。我们星月湖不是什么帮会宗派,大家都是岳帅身边的人,岳帅离开后不愿分开,才聚在一起。大哥孟非卿,二哥侯玄,谢艺是我三哥,我排行 第八。说实话 ,我们这些人里,会做的生意没几个。只不过手下的兄弟都是军士出身,能吃苦,所以才办了船行和车马行。另外大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喜欢蹴鞠,又在晴洲办了家鞠社。”
“不是临安的吗?”
“你说七星社?”萧遥逸苦笑道∶“艺哥可能没跟你说。由于岳帅的死因,我们八兄弟分成两派,二哥侯玄、七哥王韬,还有我认为岳帅并没有死,四哥斯明信、五哥卢景和六哥崔茂认定岳帅已死,发誓要报复岳帅的仇人。因为这样,四哥和二哥闹的不说话。艺哥在晴洲伤了心,才远走临安加入七星社。”
程宗扬问道∶“你认为岳帅没有死?”
萧遥逸眼神一瞬间变得锋利无比,彷佛出鞘的利剑,决然道∶“见到岳帅遗体之前,我绝不信岳帅已经过世!”
萧遥逸神情激昂起来,“岳帅生前已经没有敌手!宋主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小儿,岳帅兵权在握,又立下大功,谁能撼动他的地位!宋主一封诏书,岳帅就慨然赴死,以为岳帅是傻的啊!我萧遥逸绝对不信!”
这个世界里,岳鹏举的宿命之敌秦桧正在自己手下办差,听萧遥逸的口气,高宗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即使以宿命论,岳帅也不该死。
程宗扬摸了摸下巴。“也许岳帅对那位宋主忠心耿耿呢?”
“忠心个屁!”萧遥逸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岳帅当初差点把宋主的母后收为姬妾,后来觉得名声不好,才没有大张旗鼓的娶韦太后过门。”
程宗扬又惊又笑,“还有这种事?那位韦太后答应吗?”
“岳帅决定的事,哪儿有她说话的分。不过岳帅那段日子有一半时间都在宫里住。直到韦太后肚子大了才搬出来。”
程宗扬心里一震,“岳帅还有个女儿?”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王哲托自己照料岳帅的后人,原来以为只有月霜一个,现在不但多了个小紫,还蹦出来一个没听说过的女儿。月霜是想杀自己没杀死,小紫是自己想上没上成,这两个已经够自己头痛的了,剩下这个鬼知道还会出什么妖蛾子。
“可不是嘛。”萧遥逸颓然道∶“岳帅三个女儿,一个被王哲王大将军在军中抚养,一位就是这个没有名分的小公主,岳帅死时她才三岁,可能宋主觉得脸上无光,把她藏起来,后来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还有一个,我们刚刚才知道是在南荒。”
“艺哥离开星月湖的时候,骂我们可耻,让岳帅的子裔飘零四方,对不起岳帅,骂的一点都没错。可王哲执意不给,我们也没办扶。韦太后生的又不知下落——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干,我和五哥还去找过韦太后,可一问她就哭,我们总不好对岳帅的女人动刑吧。最后这个……”
萧遥逸说着忽然离席,对程宗扬深施一礼。
程宗扬连忙道∶“这可不敢当。能在南荒找到小紫都是谢艺的功劳,跟我没什么关系。”
“程兄客气了。我是谢公子的人品,”萧遥逸叹道∶“岳帅这个女儿美貌绝伦,程兄却能相守以礼,小紫姑娘至今还是完璧之身吧?程兄如此光风霁月,令小弟佩服得五礼投地。”
程宗扬眼圈差点红了,萧遥逸如果不提,他还不知道自己竟然这么高尚。这事不是自己够君子,实在是小紫太狡猾……
程宗扬抹了抹眼睛,大度地说道∶“这一路确实是千辛万苦,不过都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萧遥逸笑着挤挤眼睛∶“程兄这一路和尚当得够辛苦,今晚定要让程兄好好乐上一乐。芝娘。”
芝娘在下面娇滴滴应了一声。“小侯爷,酒菜来了。”
小婢捧着酒菜上来,放在案上。
萧遥逸道∶“这种小盏如何尽兴?换大盏来!”
不多时,小婢送来大盏。萧遥逸屏开小婢,亲手给程宗扬斟酒,一边笑道∶“芝娘的画舫在秦淮河只能算平常,达官贵人去的画舫都是三五层高的楼船,我不惯里面那些娼妓拿矫作态,写写诗弹个曲就用一晚上,花了上百银铢,连手都碰不着,还自称风雅。我当不得那种冤大头,还是在这里自在!”
这位小侯爷果然是个趣人,程宗扬不由抚掌大笑。
萧遥逸扯开衣领,豪气万丈地说道∶“程兄,今晚我们不醉无归!”
程宗扬也不推辞。他拿起酒盏,目光从萧遥逸颈中扫过,不由一顿。
萧遥逸脖颈上刺着“有种”两个字,上午自己只看到萧遥逸的侧颈,这会儿才发现“有种”后面还有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句话∶“有种朝这儿砍”!
那几个字书法不算上佳,但写得飞扬跋扈、狂气十足,“砍”字最后一笔还被勾画成一把滴血快刀的形状。配上那句话的口气,很有种兵痞的无赖风采,与萧遥逸这种公子哥的风流之态反差极大。
程宗扬一见之下,禁不住放声大笑,指着萧遥逸的脖颈道∶“萧兄怎么想刺上这句话?”
萧遥逸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脖颈,“我到星月湖那年才十岁,岳帅让我住在他贴身卫士的营帐里。那天我一进去,就看到六七个老兵正在玩一种纸片,他们都精赤上身,脖颈、胳膊、大腿、后背都带着刺青,嘴里骂骂咧咧全是粗话。有个脸色阴沉的汉子打输了,二话不说,拿刀就在胳膊上划了一道,鲜血淋漓,可真把我给吓住了。”
“我在旁边大气也不敢出,不小心放了个屁,被个大胖子狠瞪一眼,差点吓得我尿裤子。后来一个粗豪的汉子过来,问我是不是萧遥逸,我说是,他说他叫孟非卿,是这群人的老大。”
“孟老大跟我说,这些人都是岳帅军中的好汉,我这样白白净净像个丫头片子可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也刺个青吧。有个肩膀上刺着骷髅头的汉子就过来,说他叫谢艺,皇图天策出身,军里就数他字写得好,连岳帅也比不过他,然后替我写了这句话,让人替我刺到脖子上。”
“不对啊,”程宗扬道∶“谢艺身上没什么刺青啊?”
“可不是嘛!”萧遥逸眼圈一红,委屈地说∶“等我刺完,那帮家伙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听说我是个公子哥,故意摆出阵势来吓我。他们身上的刺青全是假的,都是拿墨写上去的。那个大胖子是侯玄,脸色阴沉的汉子是斯明信,他划那一刀也是假的,弄的是鸡血。结果八个人里就我有刺青。”
程宗扬大笑道∶“谢艺也会捉弄人?”
萧遥逸悻悻道∶“他还说自己字好,其实字最好的是七哥王韬,他们太原王氏书法是家传的,真让他写这个六个字,起码值六百银铢,我也不用哭了。后来我找个机会,趁晚上把他们有胡子的全剪了,没胡子的画了个须子。本来我还想给艺哥打个耳洞戴上耳环,结果被他发现了,挨了他一顿打,我就往他被子里塞了一窝老鼠。”
萧遥逸说起自己的恶作剧,不禁得意非凡。渐渐的,他声音低沉下来,程宗扬知道他想起谢艺,心中伤感,便拿起酒盏向萧遥逸一敬,一饮而尽。
这时他已经不再怀疑萧遥逸的身份,只不过……“萧兄十岁就到了岳帅的大营,这年龄真够小的。”
“还不是因为我爹,”萧遥逸抱怨道∶“老头儿怕我在家里跟那些人一样学成废物,哄我说有个姓岳的,那里好玩,才把我骗过去。”
程宗扬想起遇到的王谢子弟,“是那些涂脂抹粉的家伙?”
“可不是嘛。那帮子弟大都是些饭桶,行动脂粉不离手,还自负得很,整天拿个拂尘东游西荡,说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真到做事的时候连屁都不会!”
程宗扬笑道∶“听说建康的贵族盛行服食五石散?”
“五石散是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种石头制成,岳帅当年也制过,到底没敢服用。建康城服的人倒是不少。五石散服过之后身上先热后冷,还不能吃热食穿厚衣,不管天多冷都要穿单衣,喝凉水,有些还要伏冰卧雪。而且服过之后要多走,称行散,停下来就要多喝酒,多吃东西。”
萧遥逸给程宗扬斟上酒,笑道∶“五石散那东西,服之令人神智恍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上次我去阮家,正遇上阮家兄弟在服五石散,他们服过五石散,然后先用凉水冲澡,接着开始饮酒。喝到一半,阮家兄弟觉得用杯子不过瘾,用个七尺的大盆盛满酒放在院子里,诸阮就围着盆子狂饮。正喝着一群猪过来,阮家兄弟也不嫌脏,就和那些猪挤在一起饮酒。饮到兴起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妾婢叫来,在院里交相淫乱。”
萧遥逸笑着摇头,“我萧遥逸再荒唐,也荒唐不到那地步。可大家提到阮家兄弟就说他们是狂狷天性,风流人物。提起我这位小侯爷,大家都说是不成器的荒唐子弟。这也太不公平了!”
程宗扬笑道∶“这多半是因为小侯爷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吧。”
萧遥逸大笑道∶“不错!程兄果然是萧某知己!诸阮的狂狷我倒不在乎,礼法岂是为吾辈所设!但不做事还要搏取好名声,这就太过分了。那些无知小子怎能缚住我鲲鹏之翅!”
萧遥逸举盏一口喝干,把酒盏扔到几上,叫道∶“芝娘!我要的佳人呢?”
芝娘上来,未语先笑∶“小侯爷莫急。我已经让人去接丽娘,就快到了。”
萧遥逸道∶“怎么不在你舟中候着?”
“丽娘吃不得苦,在舟上两个时辰就要靠岸歇息。”芝娘笑着向程宗扬解释,“奴家画舫新来了个粉头,名叫丽娘,年纪虽然略大了些,却是好风情,遍体风流。少顷来了,让她敬公子一杯。”
萧遥逸一把搂住芝娘,把她抱在膝上笑道∶“那个丽娘就让给程兄,今晚你陪我好了。”
芝娘笑着拈起一粒葡萄,含在唇间送到萧遥逸嘴里,低笑道∶“秦淮河三千画舫,粉黛无数,小侯爷这样的人才,那些粉头便是倒贴也肯。小侯爷却总照顾奴家的生意,奴家感激不尽。让奴家陪一晚,是奴家的福气。”
萧遥逸抹了抹她鲜红的唇瓣,笑道∶“嘴巴可真甜。我喜欢你这里是免得撞上熟人,让他们整天在我爹耳边聒噪。何况还有芝娘你这样的美人儿。”
芝娘却羞涩起来,柔声道:“奴家去更衣,再来陪小侯爷。”
萧遥逸放开她,与程宗扬饮了几杯,才道∶“芝娘这里酒菜从不掺假,而且嘴巴极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从不多说。还有一桩……”
萧遥逸好看地一笑∶“芝娘这人其实做不得这营生,她心肠太软,从不打手下的粉头。若不是我,她这画舫早就关门多时了。”
程宗扬笑道∶“看不出萧兄还这么怜香惜玉。”
萧遥逸大笑道∶“这话我爱听,来,程兄,我敬你一杯!”
两人推杯换盏,谈笑无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