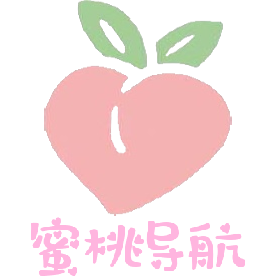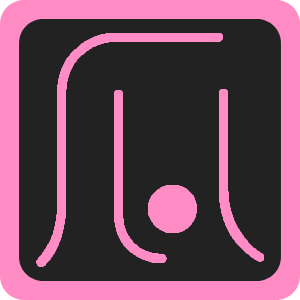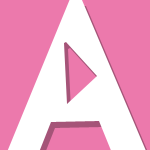站长推荐
星空入口
帝王会所
蜜桃导航
黑料福利网
吃瓜黑料网
第一导航
萝莉岛VIP
暗夜入口
小嫂嫂导航
猛男研究所
狼友福利网
黑料概念站
欲女自慰馆
万色广场
外网禁区
51福利网
TikTok入口
熟女超市
秘密研究所
全球福利汇
乱伦偷拍网
福利淫地
91福利社
初一小萝莉
换妻会所
中文情色网
三千佳丽
B站入口
隐秘部落
色色研究所
热门搜索
站长推荐
[乡村]杨家洼情事-16
第三十四章
吉庆和二蛋儿把船小心奕奕地寻了个缝隙靠了码头,找个地界儿拴好,抬着两筐鲜鱼上了岸。让吉庆和二蛋儿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小哥俩抬起头,竟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人聚过来问了:“这鱼卖么?”
“卖啊卖啊。”吉庆忙迭迭地点头。
“咋卖啊?”又有人问。
吉庆和二蛋儿互相对视着,心里都没个准谱,一旁的人又开始催了:“紧着紧着,咋卖啊,说个价。”
还是吉庆,想起了宝婶儿说过的话,咬咬牙却还是有些心虚地应了一嘴:
“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都这个价?”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问。
吉庆忙说:“不是,胖头鱼一块,小鲫瓜子便宜,看着给点儿就行!”
胖男人哦了一声儿,猫腰在筐里面翻着,吉庆忙凑过去:“叔,不用看,都是活的,早末晌刚打下来的,没歇着就送来了。”
胖男人点点头,支起身子,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庄儿的?”
“杨家洼的。”
“杨家洼的?”胖男人凝神看了看吉庆,扑哧一下乐了:“这孩子,张嘴就来。这里卖鱼的,十个有八个都说是杨家洼的,有几个是真的?!”
吉庆倒有些懵了,杨家洼就是杨家洼,咋还蒙你不成?这杨家洼又不是啥大地方,咋还有真的假的?吉庆一时间竟不知怎样说了,张个嘴嗫嚅了半天。
“你看看,撒谎了不是!这孩子,咋也会这个?”胖男人看着吉庆六神无主的模样,瘪了瘪嘴,摇着头就要走。
“谁撒谎啦,杨家洼就是杨家洼的,儿唬你!”吉庆见胖男人一副不屑的模样,立时有些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大声喊了出来。
胖男人被吉庆的声音吓了一跳,回过身,瞅着吉庆红头涨脸的模样,还是有些不信:“真得?”
“真得!儿唬你!”吉庆拍着胸脯子信誓旦旦。
胖男人扑哧一下又乐了,一边扒拉着围在鱼筐边的人,一边对吉庆说:“中中,我信,我信。”一边对聚在身边的人们吆喝着:“别瞅了别瞅了,我要了,包圆儿!”
“包圆儿?”吉庆的心要跳出了腔子,兴奋地瞅了瞅在一边的二蛋儿一眼。
二蛋儿抹着汗,也是一脸的惊喜。
“真得?叔,你都要了?”
“都要了!”胖男人豪爽地说:“就你说的价儿,大得一块钱一斤,小的给你七毛,咋样,不亏吧?”
“中中!就按叔说得算!”吉庆和二蛋儿忙不迭地点头应着。
胖男人嘿嘿笑着,走到一旁,变戏法似地抄出一杆秤来。秤杆很长,一头是沉甸甸的秤砣,另一头当啷着绳子,绳子尽头没有秤盘却是个大钩子。胖男人回身又拿出了小盆,盆子上用铁丝吊了个把手,秤钩便钩住了,然后一条条的从筐里把鱼拿出来放上去去,抬头催着吉庆:“来来,帮忙过秤。”
吉庆答应一声儿,蹲下身子帮着,一起把鱼一盆一盆的过了秤,又一盆一盆地转进胖男人自己带来的筐里。
“看好喽啊,大得这筐一共是二十四斤,小的这筐十二斤,记住喽!”
“听叔的,说啥是啥!”吉庆也认不得那秤,只会点头儿应了。
眼看着所有的鱼都过了秤,胖男人这才松心地直起身子,掏出根儿烟叼嘴里,划火柴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你们哥俩放心吧,你们可着俵口县打听打听去,我胡胖子从不干缺德的事,不亏你们。”
“信信,哪能不信呢,叔说啥是啥。”吉庆咧嘴笑着,颤颤巍巍地伸了手,心里通通地跳着,嘴巴张了张。
胖男人看吉庆那一脸为难的样子,突然醒过闷来,呵呵笑了:“忘了忘了,还没给钱呢。”说完,忙在兜里掏出了一叠皱皱巴巴的票子,一五一十地点给吉庆:“数数,没错吧?一共是三十二块四,给你三十三!”
“没错没错,谢谢叔了。”吉庆忙接过来,看也不看就塞到兜里,用一只手死命的按着,似乎怕进了裤兜的钱又会从里面飞出来。
“那成,就这样了。记住喽,下回有,还给我留着,甭给别人!只要到这来,随便找个人问,就说是公安局食堂的胡胖子,谁都认识,听着了么?”
“中中,给叔留着!”吉庆爽快地答应着,抹头拉着二蛋儿就往回跑,跑了几步,突然想起来,船舱里还有一篓子鸭蛋,忙又停住步子。回身见胡胖子正把鱼筐往自己的三轮车上搬,急忙回来帮着一起放好。
“咋又回来了?还不放心?”胡胖子问。
“不是,叔,我船上还有鸭蛋呢,叔要么?”
胡胖子问:“鸭蛋?啥鸭蛋?”
“野鸭蛋啊,那可是好东西呢!”
“野鸭蛋?真得?!”胡胖子瞪大了眼。
“可不是真的么!一早拾来的,二十多个呢。”
“那赶紧着啊,给我拿过来!”胡胖子一听是野鸭蛋,立码兴奋了,这玩意当真是好东西,拿钱都买不来。
吉庆忙捅了二蛋儿一下,二蛋儿飞一般的跑回到船上,一会功夫就拎着装满鸭蛋的篓子尥了回来,喘着粗气递给胡胖子。胡胖子高兴地拿出一枚,对着阳光看,看完了又拿出一枚。
“不蒙叔,真是野鸭蛋呢。”吉庆怕胡胖子不信,忙紧着解释。
胡胖子嘿嘿笑着:“信!哪能不信呢,看你们都是老实孩子,干不了那蒙人的事儿。”
“叔说得对呢,我们都是头一回卖这些,啥都不懂,往后还要求叔多照应着呢。”吉庆眼巴巴地望着胡胖子,胡胖子瞥了一眼吉庆,却越发觉得吉庆眼神中的那种质朴和真诚竟是那么熟悉。
胡胖子也是从乡下上来的,在市面上混了那么久,这样的质朴却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胡胖子突然地想起了自己在乡下的家,突然地想起了乡下那些儿时的玩伴,也突然地对吉庆有了一种没来由的喜欢。有时候人跟人就是这样,也说不出个啥缘由,很多时候也就是一照面的功夫,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了好感。
胡胖子笑着点头,把鸭蛋放回了篓子里:“照应谈不上,往后来,有啥事儿找你叔就没错了。我这也是看你们对上眼了,啥也不说了,说个价吧。”
“叔说,听叔的!”
“那中,三毛吧。”
“中!”吉庆爽快地应着,顺手拿起了胡胖子车上的秤。
胡胖子看吉庆拿起秤杆子,扑哧一下又笑了:“你们也就是碰见我了,要是别人,把你们卖了你们还得乐呢。”
吉庆不明白胡胖子的意思,拿着秤愣在了那里。
“这个傻小子哦,我说的三毛,是一个三毛,你拿个秤干啥?按斤要(yāo)啊。再说了,三毛一斤你就卖?鸡蛋还一块五一斤呢。”
“一个三毛啊!”吉庆这才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可不么,一个三毛和一斤三毛那得差多少钱呢,幸亏遇到了好人,不然可亏大了。
“紧着数一下,看看多少。”胡胖子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爽快地吆喝着。
吉庆和二蛋儿屁颠屁颠地两个两个的过了数,心里的小算盘扒拉得稀里哗啦,几乎要美出鼻涕泡。
回去的路上,顺风顺水。
初战告捷,小哥俩被满心的欢喜鼓舞得像吞了热豆腐,一刻也不得消停。二蛋儿的撸摇得轻快,吉庆站在船头一脸的昂扬。
卖鱼所得是三十三块,再加上鸭蛋的七块钱,整整四十。
吉庆手心里捧着,一张一张沾了唾沫数了又数,却还是舍不得揣进兜里。长这么大,吉庆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这一摞有零有整脏呼呼的票子,在吉庆眼里,却不亚于一座金山。
吉庆重新又数了一遍,数过了又仔细地平均分成了两份,把自己的那份掖回了兜里,回身把二蛋儿那份递了过去。
“这是给我的?”二蛋儿停下了摇橹的胳膊,双手在自己的衣服上使劲的蹭了蹭,用了小心地接过来,一张圆呼呼的脸因为兴奋显得红润而又激动,本来不大的小眼儿,看到了钱却陡然瞪成了个铃铛。
“你点点,一共是四十块钱,咋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吉庆洋洋自得地坐在船头,赤裸的脚丫子探进水面,啪嗒啪嗒地踢弄着。
二蛋儿喜悦地“哎”了一声儿,却也没数,直接就揣进了兜,想了想,却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重新又把钱掏了出来,嘟囔着嘴说:“庆儿,不好吧,咋给我这么多呢?是你带着我弄得,咋说,也得拿大头儿啊。”
“啥大头儿小头儿的,是我俩一起弄的,当然得对半分。”吉庆说。
“不行不行,”二蛋儿数了几张捏在手里,凑过来,死活地往吉庆手里边塞:“我就是搭把手儿,谁都能干的活儿!”
吉庆忙往外推:“话咋能这么说呢,再说了,船还是你的呢。”
二蛋儿还是有些不依不饶的,两个人就在这狭小的船上你推我搡地挣扒了起来,把个小船弄得晃晃悠悠左颠右闪。吉庆有些恼了,一把将二蛋儿推了回去:
“你咋那么多事儿呢,本来就是两个人搭伙,分个钱还磨磨唧唧的!”
二蛋儿看吉庆真得有些上脸,手里面攥着钱竟有些手足无措,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嘀咕:“不合适,真不合适。”
“行了!就这么的了!”吉庆大手一挥,扭过脸去继续坐在船头,再也不理会二蛋儿。二蛋儿看吉庆一副坚决的样子,也只好回到船艄,把撸拎起来怏怏地摇着,心里却还是惴惴地。
吉庆表面上生气,其实心里还是有些美滋滋的。人们常说,看一个人得从钱上来看,关键时候这个人不贪,那人品基本上就没跑了。吉庆长这么大没见过也听过,农村人家家都穷,把个钱财看得更重。多少家为了一点财产打个头破血流的,有的亲哥们都反目成了仇。杨家洼里和吉庆好的伙伴们成群结队,但都是一帮孩子,还没在钱财上有过啥牵扯。这是头一回在手里面过了钱财,也就是这头一回,吉庆基本上肯定了二蛋儿是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经过这一次顺风顺水的经历,吉庆陡然之间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再加上有了二蛋儿做帮手,吉庆一时间更是志得意满。就好像金山银山就摆在眼前,伸伸手就能搂进怀里一样。
想到这些,吉庆心里面被一种燥动鼓弄得有些手舞足蹈,看着波光鳞鳞的河水,恨不得跳进去扎上几个猛子,忍不住张嘴唱了起来。二蛋儿听见吉庆声嘶力竭的嚎叫声儿,嘿嘿地乐了,扯着个破锣嗓子也跟着唱起来。
两个人的歌声在寂静的河面上回荡着,那声调倒像是被风扯着的风筝,忽高忽低此起彼伏直冲云霄。两岸浩浩荡荡连绵不绝的苇丛中,成群结队的水鸟被惊醒,呼啦啦地飞起来,鸣叫着四散盘旋。
小哥俩就这么唱着闹着欢笑着,远远地河道拐弯儿处,杨家洼高高低低的房脊很快便隐隐显现出来。
大脚打早上一起来就没见到吉庆的人影,晌午饭都没回来吃,心里头来气,这时候正摔摔打打地嘀咕着。长贵和往日里一样,眼瞅着大脚的心气不顺,吃过饭便不声不响地溜了出去。
大脚一个人屋里屋外地踅摸,竟是看什么都有气,嗓子眼就好像吃了南傍国面的窝头,上不来下不去地堵得难受。好几天了,大脚就像在地里面轰麻雀的那根栓了红绳的麻杆儿,吉庆却似那些猴精猴精的鸟,饶是任大脚围追堵截的,竟愣是没个办法。不是推就是躲,把个大脚闪得七上八下的,气馁之余就觉得自己个真是犯贱。有时候也咬着牙在心里面骂,连带着那院儿的娘俩儿。骂过了就恨恨地和长贵折腾,心里面恍恍惚惚地把长贵当了吉庆,可着劲儿地拽在自己身上再不下来,把个心气十足的长贵也累了个够呛。可那股劲儿松了,气喘吁吁地躺在炕上,那吉庆的影子却又倔强地从心里头冒出来。大脚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的想,想和吉庆在炕上痴痴缠缠地情景,想吉庆伏在自己两腿间汗流浃背的模样儿,越想却越是百爪挠心。
抬头看看早就偏了头顶的日头,大脚嘴里面骂着,把个鸡食盆子“咣当”一下,扔在了当院,弄了个鸡飞狗跳。本以为吉庆又跑到隔壁了,可上午巧姨颠颠地过来串门,竟说也没看见。
屋里头的座钟“铛铛铛”地响了一串,大脚终于再也待不下去,扭身出了院子。
巧姨正出来泼水,扭头正看见大脚怏怏地掩门,站住身问:“庆儿还没回来?”
“鬼知道死哪去了!”大脚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那你这是要去哪?”
还真是的,自己这是要去哪呢?大脚被巧姨这么一问,却愣住了,想了想,说:“去找找,没准又下河洗澡呢。”
“洗澡还能洗上一天啊,没准去找同学玩了呢,”巧姨说,又招呼大脚:
“别去瞎找了,一会儿庆儿回来再撞了锁,来,上我这儿待会儿。”
“你那儿有啥好待的。”大脚嘴里面小声嘀咕着,却还是走了过来。
大巧儿和二巧儿正在院子里的菜园子摘菜,见娘和大叫一起进来,齐齐地叫了一声儿“大脚婶”,大脚僵硬的脸这才松弛了下来,硬挤着堆出来一丝笑容。
巧姨抄了个马扎递给大脚,大脚坐了,却还是扭头冲着外面张望。
“诶呀行了,咋就那么惦记,一会儿看不着就想了?”巧姨也坐在大脚身边,笑着调侃她。
大脚心里面有鬼,巧姨无意的一句话,但在大脚耳朵里却格外刺耳。心里面激灵一下,回头看了看巧姨,见巧姨一张笑脸并无异状,这才放心,却还是忍不住回了一嘴:“我的儿当然我惦记,有人却不知道惦记个啥呢。”
巧姨本就是个玲珑剔透的女人,感觉着大脚话锋不对,问:“我咋听你话里有话呢,哦,我不该惦记?咋说也是我未来的姑爷呢。”
“该该,谁敢说你不该呢!”大脚哼了一下,给了巧姨一个白眼:“就怕不该惦记的地界儿也瞎惦记!”
巧姨心里也是一紧:这大脚的话越发让人难懂了,莫非和吉庆的事情被她知道了?巧姨脑子转得飞快,表面上却仍是波澜不惊的模样,满脸堆着媚笑,竟还往大脚跟前儿凑了凑:“你倒是说说,那啥地界儿该惦记,啥地界儿又不该惦记呢?”
大脚倒一时哑口无言了,暗暗懊恼自己这压不住的性子。难不成把这个脏事儿就此撕破了?别到时候扯出肠子带出了筋!想到这里,竟也无可奈何,只好胡乱地支吾着:“中中,你都该惦记!明个把那兔崽子绑你裤腰上,行了吧?”
巧姨“格格”的倒乐成了一团:“那敢情好,我还白赚了呢,省得到时候疼姑爷还得去你那边现喊。”
大脚更是气恼,也不知道这巧姨是不是在装傻充愣,恨不得上去拧她那咧到后脑勺的嘴。好在老姐俩从小到大也是闹惯了,你来我往的却也没真的上脸,依旧稳稳地坐了,远远看去倒和往日里两人插荤打磕没啥两样儿。
大脚瞥了一眼在那边干活的小姐俩,压低了声音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你个骚货,你就成天的浪笑吧,等哪天把你那窟窿堵上,让你还笑得出来!”
巧姨笑得更是欢畅,一连串银铃似的笑声悠扬顿挫,惹得大巧儿二巧儿止不住地看过来。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懒得理你,走了!”
大脚站起身来,甩搭甩搭地就要走,却被巧姨一把拽住:“等会儿等会儿,还没说完呢。”
“有事儿?”大脚停住,扭头看了一眼巧姨。
“你坐下,坐好喽,”巧姨一把将大脚扥下,按在马扎上坐好,诡异的一笑,小声问:“我觉着你这些日子不对劲呢?是不是有啥好事儿?”
大脚诧异地低头看自己,疑惑地问:“啥不对劲?你看我哪像是有好事儿?”
“天天耷拉着一张脸,倒是看不出有啥好事儿。”巧姨抿嘴笑着,脸上越发的神秘兮兮:“不过,看你这神态,咋瞅咋像是犯了桃花呢。”
大脚“呸”地一声儿,啐了口吐沫:“你个骚嘴,天天的就是这个!桃花咋长也长不到我这来,倒是你吧,赶紧摘摘自个,快被桃花埋起来了!”
巧姨格格一笑,凑近了大脚:“真得真得,说真格的呢,你自己不知道,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看看你,这屁股也圆了,奶子也鼓了,这老脸都跟抹了蜜似地,天天带着红润呢!”说完,闪了身子上下打量着大脚,越瞅脸上的戏谑嬉笑却是越浓。
大脚被她看得糊涂,也自己扭着身子上下地看,终于惴惴不安地问:“这真能看出来?”
巧姨“嘎嘎”地笑弯了腰,指着大脚:“你看你看,不打自招了吧……”
大脚立时醒过闷来,这是被巧姨调理了,一脸的羞臊,“诶呀”一声儿,站起身来就要撕扯巧姨。巧姨笑着去躲,姐俩个倒像是一对没出门的闺女,嘻嘻笑着扯成了一团。一边的大巧儿二巧儿不知道这边是为了啥,却也被两人的无忌感染了,呵呵地跟着笑。
两个人闹了一会儿,总算消停了下来,巧姨搂着大脚,凑在她耳边问:“说说,咋回事?”
“滚犊子,啥咋回事?!”大脚摩挲着胸脯,喘个不停。
“还装!跟我你还没个实话呢。”
大脚一时语噎,不知道跟她说是不说。想了想,却觉得这些日子吉庆被她独占了,无论如何地心有不甘,陡然而生一阵子嫉妒。索性说了,好歹也是个让她羡慕的缘由。眼睛悄悄地往菜园子方向抽了一眼,掩了口凑在巧姨耳边:“长贵好了!”
“真得?!”巧姨一脸的惊奇,装模作样的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
“可不真的,这事我蒙你干啥!”大脚洋洋自得地坐下,下巴颏扬起老高,到好似对巧姨示威一样。
“说说,说说!”巧姨拽着自己的马扎凑得更近:“说说他是咋好的!”
“谁知道咋好的,冷不丁就好了呗。”大脚闪烁其词,却再不敢把长贵治病的偏方说了出来。
“蒙鬼去吧!说好就好了?”
巧姨撇着嘴,满脸的不信。大脚一副爱信不信的模样,却再不敢接茬,忙扭脸去瞅门口。门外的街道依旧是静悄悄的,远处高高低低地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尖利的声音此起彼伏。树叶好像是被毒辣辣的日头晒得焦了,有气无力地低垂着,风也没有一丝儿,越发显得燥热。
老姐俩依旧是默默地坐着,一个是打破沙锅要问到底的神态,另一个却倔强个脖子任你大刀片砍来,依旧是是岿然不动。一时间倒有些僵了。
吉庆就在这时,恰如其分地跑了进来,满脸的汗水,气喘吁吁。
吉庆像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旋风,撒着欢儿冲进了门。本要大声喊上一嗓子的,却猛地见到院子里坐着的两个女人,竟生生地把将要喊出的话咽了回去,就那么傻呆呆地愣在那里。
大脚乍一见吉庆,像是见着了救星,悬了半天的那颗心“扑通”一下落回了肚,猛地站起身,几乎要扑了过去,恨不得把吉庆死死地拢进怀里。巧姨在她身后却先开了腔:“你看看,让你别着急不是?这不是回来了!”
大脚“噔噔噔”地抢步上前,一把拽着吉庆:“这大半天儿的,你这是去哪儿了?”
吉庆还没缓过劲儿,被娘拽着,只是一个劲地气喘,却说不出个话来。本是想赶紧着把兜里的钱塞给巧姨,也让她高兴一下,没成想咋就看见了娘。吉庆不知道娘的心思,可不敢把去县里卖鱼的事情,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说了。虽说娘和巧姨是发小的交情,但这么多钱搁手里,任谁都会打个磕巴。别到时候娘再不愿意,那自己夸下的海口就再也没法子兑现了。
大脚仍是拽着吉庆不撒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吉庆的脸被汗水打得精湿,七凌八道儿的,衣服上点点块块地泥巴洇着水渍,看起来像是从水坑里打了个滚又钻出来一样。
大脚“啧啧”地看,胡噜着吉庆的褂子:“你瞅瞅,你瞅瞅,这是去哪滚了?
你看看这一身的泥!“吉庆老大不小了,站在那里像座山高,被娘这么翻来覆去地摆弄,着实地有些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闪躲,不时地偷看一眼巧姨。巧姨却是一脸嫣然地笑,和吉庆对眼神儿的功夫,还不忘悄悄地撅了嘴虚空里亲上一下。
大脚却没理会吉庆的不耐,又捏着袖子在吉庆的额头上擦着:“出去一天,也不跟娘说上一声儿,吃了么?”
大脚要是不问,吉庆还真是忘了,从早上到现在,竟是水米未进,这才发觉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大脚似乎也听见了,伸指头杵了吉庆一下,嗔怪着:“饿了咋不知回家吃饭呢?紧着!”说完,拉着吉庆就往外走。
吉庆被大脚连拉带拽地出了门,头却扭着,眼巴巴地瞅着巧姨。巧姨还是笑滋滋的,朝他扬扬手,却没再说话。
街上的知了依旧鼓噪地叫着,吉庆的心里头却比这此即彼伏的鸣叫声还要心烦。本是个皆大欢喜的场面,没成想就被娘给搅了。回来的路上,吉庆还一遍遍地勾勒着,这头一次把挣到的钱递给巧姨的场景,想象着娘仨个喜悦的笑脸和对自己的那种钦佩。
这是吉庆最憧憬的事情,自打和巧姨娘俩个有了那事儿,吉庆从来是索取却没为这些孤儿寡母地出过一分力。好不容易自己真正的像了个男人,却没有最快地享受这种敬佩,吉庆一脑门子的沮丧。
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娘拽着回了家,却还是僵硬着身子,大脚就像是牵了头倔驴。
娘俩个进了门,大脚手脚麻利地把桌子支在当院儿。锅里的饭菜还热着,大脚一边催着吉庆去洗涮,一边大碗小碗地端出来。
吉庆懒懒地洗完,又恹恹地坐了,啥也不说就大口地吞咽起来。大脚见吉庆吃得香甜,心里面一阵子慰藉,坐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狼吞虎咽。吉庆乌黑的头发乱蓬蓬地,大脚轻轻地拢了,心里却一阵紧似一阵地有些异样,终于轻声地嘟囔:“疯了多半天,咋不知道娘在家惦记?回来了不吭一声,却先往你巧姨家跑。”
吉庆嘴里填满了食物,也自觉理亏,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这一笑,便把大脚的心又笑得酥酥的,越发看着吉庆越发觉得哪哪都是那么的可人疼惜,不知不觉手便伸了过去,在吉庆的脸颊上轻柔地摩挲着。吉庆却下意识地一躲,躲得大脚心里一紧。
“咋啦?不稀罕娘了?”大脚心里一酸,喃喃地问。
吉庆愧疚地看了娘一眼,低了头继续把碗里的饭往嘴里扒拉。
大脚仍是幽怨地问:“到底是咋了,娘做的不好?”
吉庆摇摇头,却不敢看大脚一眼。
“那你跟娘说,娘改还不成么?”大脚拽了板凳往吉庆跟前凑,胳膊却拢上了吉庆,头斜斜地靠上去。吉庆没来由地又想去躲,却被大脚死死地拽了,吉庆不安地往屋里望去。
“你爹不在。”大脚小声地说,吉庆这才心安,也不再挣巴了,任由娘靠在自己的身上。
大脚心满意足地将头稳稳地靠在吉庆肩上,耳朵里听着吉庆脆生生地咀嚼,鼻子里闻着吉庆身上浓重的汗味儿,心里面却被一种异样填满。有温馨,还有一种躁动的酥痒。大脚就觉得大腿根儿那地方竟慢慢热了,像被这初夏的日头晒着,呼啦啦便潮润了。
大脚抬起头,嘴唇凑到吉庆耳根,喃喃地说:“快点吃啊……娘想了……”
一股子热气喷到吉庆的耳廓,炙得吉庆火辣辣地瘙痒。娘颤巍巍骚浪的声音幽幽地鼓荡在吉庆耳边,让吉庆一阵麻嗖嗖地汗毛直立,心口立时止不住地扑通扑通跳了起来。要搁以往,吉庆二话不说立刻就会拽了娘一起奔了屋里,可现在……吉庆一时间却有些手足无措。
大脚却贴得更紧,一对胀鼓鼓的奶子就像是粘在了吉庆身上,却还是死命地挤着,呼吸也愈加粗重,勾引得吉庆也抑制不住地喘了起来。不知不觉,下面那不争气的家伙竟昂起了头,把裤子顶出了一个鼓包。吉庆不安地挪着身子,还没等动上几下,那地方却被大脚的一只手捂住了,五指簌簌捻动,把个吉庆弄得立时便僵硬了身子。
“……进屋?”大脚小声儿地问。
吉庆说不出话,只是大口地喘气。侧眼一瞟,见娘一件洗得精薄的棉布小衫下,白白嫩嫩的肉若隐若现,衣领处不知什么时候敞开了几粒扣子,两团鼓囊囊的奶子挤出一条深深地乳沟。
刚刚还喝了一口汤,吉庆突然却觉得口干舌燥,一双眼竟似是长了钩子,定在娘的胸脯却再也挪不开,下身被娘一只柔弱无骨的手揉搓得像个点着了芯子的炮仗。大脚眼神越发迷离了起来,手里面加紧弄着,嘴里竟喘着“哼”了一声儿,也不嫌热,把个丰腴的身子更紧地贴实了吉庆。
吉庆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里就剩下了娘那一抹白嫩嫩的肉,先前的那些顾虑早就跑到了大河对岸,一只手颤微微就放下了碗,顺着大脚敞开的领口就伸了进去。大脚捏着嗓子悠悠荡荡地“啊”了一声儿,身子立马软得扶不成个,却还是挺着胸脯子,让吉庆的手囫囵地抓个满满实实。
吉庆汗渍渍的手罩在娘松软的奶子上揉搓着,感觉娘喧腾腾的胸脯愈加滑腻,两粒奶头拨楞了两下便鼓鼓地挺在了那里,每次吉庆的手划过,大脚的身子便忍不住地抖上那么一抖。抖着抖着,那大脚更加酸软无力,那股子邪火像一群裹挟在烟囱里的马蜂,在身子里乱撞,刺挠得大脚愈发把持不住,依靠在吉庆怀里,抬了眼皮,有气无力的只会催促:“庆儿……进屋?……进屋吧。”
娘俩个好些日子没这样坦诚相见了,大脚自不必说,每天里想儿子想得不行不行的了。就是吉庆,虽然有巧姨和大巧轮换着鼓弄,但闲暇里或多或少还是惦记着娘,一想起和娘裹在一个被窝里嘘嘘嗦嗦地那份热乎,心里也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刺痒。都是女人,在吉庆的心里,却不是一个味道也不是一个感觉。巧姨骚浪大巧儿乖巧,而娘这边,却是实打实的是一份刺激。
说实在的,要是没有爹在,或者说爹还是以前那副身子骨,吉庆倒是想和娘再多弄上几回。就像是地里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撒开了让他吃,也没啥子味道,可黑下里从别人家菜园子偷来的,那嚼一口,从里往外的一股子清香。就是不一样。可吉庆自认不是个混蛋,虽然和娘睡了跟个畜生也差不多了,但吉庆在心里还是有台阶可下:自家有自家的难处,自己做出了丑事也实在是没法子,咋也不能让娘去外面偷人不是?每每想到这些,吉庆一下子变得坦然,也更理所当然的享受起了这种刺激。
可自打瞅见爹的身子骨又好了,吉庆难免有些失落。失落之余,却告诫着自己再不能和娘不清不楚的了。师出无名,这事儿再做起来,想一想却总是让他心虚。
今天这是咋了?那股子邪火又像是浇了油一般地窜起老高,竟是再也熄不灭的劲头。娘还在身边鼓悠着,丰满滑腻的肉一堆一块,颤颤微微地哆嗦着,那嗓子眼儿还是和以前一样,哼哼唧唧,像把挠子,直接伸进了吉庆的腔子里,把里面的心啊肺啊梳理个遍,越梳理却越是让吉庆像个烧红了的烙铁。
啥也不管了!吉庆再也熬不下去,啥应该不应该的也丢了个干净,“噌”地站起来,拽着已经有些五迷三道的娘就往屋里走去。
屋里静静地,日头已经从头顶斜了下去,被院里的树荫遮着,灼人的光再也打不进来。前后的窗户都敞着,有微微地风缓缓吹进来,显得清凉干爽。
大脚被吉庆跌跌撞撞地拉进了屋,看到清凉的炕终于支持不住,一个趔趄便仰了上去,却还张着个手伸着胳膊冲吉庆站着的地方招呼着。吉庆站在炕下,看着娘一副慵懒无力的身子,躺在那里还轻轻地抖动着,越发难耐,三下五除二地便扒光了衣裳。大脚这才醒过闷,也紧着把自己本就不多的衣裳也抽胳膊缩腿地褪了下来,白花花软乎乎地身子立时敞在了那里,急慌慌擗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腿,眼巴巴地等着吉庆上来。
吉庆没上炕,却迫不及待地蹲在了炕沿,扳了大脚两条腿往下去拽。大脚会意,忙扭着屁股把身子垫着往外挪了挪,凑合着吉庆伸过来的脑袋。
一股股热气随着吉庆粗重的喘息喷在大脚大敞四开的下身,让大脚想起了发情时的狼狗打着响鼻儿在母狗的阴户嗅着的样子。那母狗一定也和自己个一样吧,揣着个“噗噗”乱跳的心,又期待又紧张地等着?
大脚的胸脯起伏地越发急促,喉咙里努力地压着却还是挤出一丝丝呻吟,毛毛眼半闭半张,迷离而又恍惚地眼神儿越过自己暴胀的奶子和微隆起的肚皮,瞄向两腿之间儿子的脸。那张脸有些扭曲和狰狞,却让大脚感觉着即将而来的那股子拼了命的狠劲儿。那是一种让大脚几乎背过气的狠劲儿,却又让大脚着了迷。
那股子凶猛无比的碾压和揉搓,一次次把大脚从炕上送上了天,又从天上拽回了地,一上一下的功夫,就像踩在云彩里,深一脚浅一脚竟说不出来的欢畅和舒坦。
那感觉长贵给不了,只有她的庆儿!
一想起这个,大脚就从里往外的痒痒,于是把身子敞得更开,还哆嗦着蜷起腿,把肥嘟嘟的屁股往上支了一支,把个湿乎乎紧要的地界儿往吉庆的脸上凑去,像个饿极了的鱼嘴寻着吃食一样,嘴里更似断了气一般,喃喃地叫着:
“……紧着呀……紧着……”
大脚下身的毛发密密匝匝的,在吉庆眼里却比前些日子更浓了一些,那两片蚌肉一样的唇颜色也越发重了,咻咻地办掩半合,中间那条缝隙里,早已经磨磨唧唧地湿成了一片,溢出来的浆汁倒像是河蚌里的涎水,浑浊却又清亮。
吉庆附上去,鼻子在娘那地界儿嗅着。扑鼻而来一股子热烘烘腥臊的骚气,可吉庆闻起来却像是闻着烧开了的老陈醋,刺鼻却格外的振奋。吉庆的舌头伸了出来,裹弄着便卷了上去,踢哩吐鲁像是舔着盘子里剩下的肉汤儿,有滋有味儿得那么贪婪。
大脚“啊”地一嗓子叫了出来,“哎呦哎呦”地像是被痒痒挠抓到了最心急的地方,透着一股子熨熨帖帖的舒坦,舒坦得她两只胳膊死劲儿地抵着炕席,把个身子拱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桥。而头却努力地梗着,眼睛死死地盯了下面,看着吉庆的脑袋上上下下地在那里蠕动。每一次蠕动,都会给她带来一股股抓心挠肝的快活。大脚再不去管它什么青天白日,随着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尽情地叫了起来,那叫声和夜深人静时比起来并不高亢,却一样的声嘶力竭。
吉庆似乎被娘忘我的情绪感染,狼狗一样的舌头舔弄得愈加淋漓,不时地停顿一下,却还问着:“舒坦么?舒坦么?”
“嗯嗯!嗯嗯!”大脚迭迭地点头,嘴里面叫着竟连说上一声儿的工夫儿否没有了。
吉庆舔得更加卖力,两只手还凑过来,把娘的大腿擗得更开。一手扒着一片湿淋淋的肉唇,像打开一扇门远远地分了,于是那条缝儿便彻彻底底地显现出来,热烘烘敞开了一孔洞,粉扑扑却有些触目惊心。吉庆的舌头伸出了大半,拧了劲儿便塞了进去,就感觉着娘的身子一紧,像被针扎了那么一下。
吉庆听见娘的叫声突然尖利了起来,接踵而来的是娘有气无力的呢喃:“要死了……要死了……你要把娘弄死了……”
大脚的手下意识地就摸了下来,一把抓住了吉庆乱蓬蓬的头发,似乎有些难耐,情不自禁地推了推,却马上又按了下去,下身配合着挺了又挺,把吉庆的头死死地抵住了自己,倒像是怕吉庆浅尝即止就这么没了。
吉庆把舌头当做了那个物件儿,绷紧了力气由浅往深地插了,又滑出来上下地扫弄。大脚的两片肉滴滴答答却越发饱满,像是拌得了的凉粉儿被吉庆卷来卷去,那缝隙上面的一粒红红的肉丘便突兀地更加醒目,像是沟壑中杵在那里的一个山包。巧姨说过,这地界儿却是女人最要命的所在,触到了便会止不住地酥软乏力,轻易是动不得的。可每次两人腻腻歪歪地缠在一起,巧姨却总是勾引着吉庆或用手或用口的在那地界儿弄上半天,每次弄了,巧姨总是一身大汗,嗷嗷叫着胡言乱语,直到精疲力竭却总是意犹未尽。
看娘这里却不亚于巧姨,一样是红红肿肿,却比巧姨那里更加的饱满挺拔,鼓鼓囊囊地矗在褶褶皱皱之间,竟探出了老大一截。吉庆看得眼热心动,舌尖便探了上去,刚刚触到,就觉着娘的身子又是一抖,嘴里边“哎呦”一声儿。
吉庆知道娘敏感的身子这是觉察出了酥痒,更铁了心戏弄一下,于是整个嘴便贴了上去,不管不顾地把那粒肉丘整个地含在了唇间,舌头压住了像是吮住了奶头,“吸溜吸溜”地再不放口。
大脚一下子便不行了,那地界像是一个电门,按上了便刺刺啦啦地牵引了浑身,汗毛恨不得都立了起来,两只手更是抵在了炕上,把个腰拱起来老高,“啊啊”叫着哆嗦个不停。
“……可要了亲命了……”过了好半天,大脚那口气才缓过来。
吉庆却没闲着,那舌头卷得天花儿乱坠,大脚还没等喘上一口气,接二连三地快活又接踵而来,白花花的光身子忍不住又在炕上抖了起来,嘴里嚷嚷着:
“庆儿啊,庆儿啊,不行了,娘不行了……你这是让娘死啊……”
吉庆抬起头,嘿嘿笑着:“娘死不了,娘还没得劲儿呢。”
“得劲儿!得劲儿!娘得劲儿了!快……快点儿,庆儿快点儿进来吧,娘痒得不行了!”
吉庆又问:“娘这是哪痒啦?”
“屄!屄里痒了,紧着……紧着弄一下娘!”
吉庆嘿嘿又笑:“咋弄啊?”
“你个恨人的玩意儿!”大脚急了:“咋弄你能不会?鸡巴……鸡巴呢?
用鸡巴啊……““鸡巴?鸡巴咋弄?”吉庆却是一脸的顽皮,这时候的他倒是没了刚才急慌慌的样儿,竟看起了娘的笑话儿。
大脚更加焦渴,一把将自己的的两条腿扳了,把个黑糊糊凌乱不堪的下体更大咧咧擗开,梗着脖子凝眉盯着吉庆,急赤白脸地催着:“……用鸡巴肏啊,屄……肏娘的屄!”
“那娘你得求我!”
“你个恨人的玩意儿!”大脚急得几乎伸脚踹了上去,无奈却浑身无力,只好低声下气地央告:“中,中,求你了!娘求你了!你就肏一下娘,娘痒得不行了……肏吧……就肏一下……”
“这可是娘求我肏的!”吉庆笑滋滋儿站起来,拨楞着自己竖在那里像根儿炮筒子一样的物件儿。
“对对,是娘求的!娘求的!求你肏……肏娘的屄!”大脚迭迭的点头应着,把身子又往下迫不及待地拱了拱,大敞四开的。那咻咻蠕动的地方,似乎是一张饿极了的嘴,恨不得窜上去把吉庆的家伙一口叼了进去。
吉庆的手扶着自己仍是不慌不忙,戏谑地凑上前,却把个肿胀通红的头儿放在娘紧要的地方上上下下地蹭。就像个拿着香火钱的光头和尚到了山门却徘徊不前,倒把等在里面的师傅急了个半死。
“进来!……进来呀!”大脚急得抓心挠肝的,鼓悠着身子迭迭地催。
吉庆还是扶着棒槌一样的家伙,在两片肉唇之间抹啊挤啊蹭着,还不时地在上面那颗越发坚挺红润的肉蒂点上几下。每次触到,大脚就“啊”地一声浪叫,身子也是一个激灵接着一个激灵。
终于,大脚再也支持不住,心一横索性一骨碌翻身起来,劈头盖脸地就把吉庆抱在了怀里,身子一拧,便压上了炕。吉庆还沉浸在戏耍玩弄的得意之中,糊里糊涂便被娘箍在了怀里,等反应过来却早被娘死死地压在了身子底下。大脚一张口干舌燥的嘴也随之覆了过来,软呼呼地舌头也扒拉着吉庆的嘴唇挤了进去,支支吾吾地便嘬个尽兴。两个舌头在娘俩的唇间你来我往吮吸着,直到这时,大脚才咂摸出一点滋味儿,干巴巴地口里也总算有了些润滑。
娘俩个脸贴了脸辗转着黏在一起,四只手也不着闲,互相在光裸的身子上摸索揉捏。大脚更是伸下去,一把将吉庆棒棒硬别在那里的物件儿攥住,着急八慌地撸动,肥硕的屁股也早就分开跨好,鼓鼓悠悠地便凑了上去。娘俩个早就熟门熟路,大脚也不用再低头去找,吉庆也不用挺身逢迎,一凹一凸就像是久别重逢,不由分说就套了进去,又好似螺丝对了螺母,套进去便严丝合缝吞了个尽头尽尾。
大脚终于心满意足,就像是寒冬腊月里吞了口热乎乎的肉汤,浑身上下由里往外的透出一股子惬意和松爽。忍不住长叹一声,把个身子直立起来,踏踏实实地在吉庆身上坐稳,丰腴的腰却慢慢地扭了,连带着磨盘似地屁股,上下地研了一个花儿,就感觉吉庆那玩意儿在身子里仍是直直愣愣,热乎乎地捅进了心窝一般的那么熨帖。
“可舒坦死了……”大脚哽咽着挤出了这么一句,手撑住吉庆的胸脯,小心却又有些急迫地前前后后动了起来,那两只鼓囊囊的奶子垂在吉庆脸上,随着身子的摇动,晃晃悠悠摇摇摆摆,像是两口吊钟在风中摇曳。
也许是在心里对吉庆饥渴得太久,又也许是因为初愈的长贵远不如吉庆生龙活虎,大脚就觉着沾上吉庆的身子就有些不行了,更别说实实在在地捅了进去,那股子滋味儿,大脚说不出道不明却是由衷地快活。